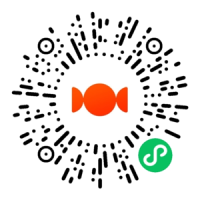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硅谷》是如何重现 “硅谷” 的?
译者按:美国硅谷一直以来都是创业者和科技从业者的圣地。但在这光鲜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硅谷》是美国电视台 HBO 于 2014 年推出的半小时情景喜剧,讲述了一群程序员在硅谷创业的起起落落。该剧以一种夸张、犀利的幽默讽刺了当今硅谷创业圈中的众生百态,业内大佬、科技巨头纷纷躺枪,让人捧腹。本文以详实的笔触采访了《硅谷》的幕后制作人员,当中不乏各种趣闻轶事,值得一读。究竟是现实中的硅谷造就了《硅谷》的诞生,还是虚构的《硅谷》促成了硅谷的转变,相信你看完之后自会有一个答案。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Dick Costolo 还在密歇根大学念计算机科学,但他奇怪地发现自己在即兴喜剧方面也有一手。毕业以后,他搬到芝加哥去第二城剧院(The Second City Theatre)上课。不像他的同学们——Steve Carell,Tina Fey 和 Adam McKay 那样,Costolo 后来没能加入剧团,他的喜剧生涯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于是他重操旧业成了一名程序员,还创办了一系列科技公司。其中一家最终被谷歌以一亿美金的价格收购。2010 年,Costolo 当上了 Twitter 的 CEO,第一年就赚了一千万美金。在一次慈善活动上,他偶遇老同学 Steve Carell。两人一起回味了当年作为即兴喜剧演员放浪形骸的日子。“真遗憾表演不是你的菜。” Carell 开玩笑说。
2015 年 6 月,Twitter 股价疲软,Costolo 宣布自己即将卸任。(据科技媒体报道,Costolo 是被董事会逼下台的;而他坚持说是自己的主意。)三天后,HBO 播出了讽刺短剧《硅谷》的第二季大结局,留下一大悬念。
身为一家科技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的男主角被自己公司的董事会开除了。作为该剧的粉丝,Costolo 发现这幕场景出奇地熟悉。他说:
“我能理解那个处境下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下台的创始人,即将上任的新 CEO,还是目睹一切的员工。”
那个时候,Costolo 在旧金山跟 Kara Swisher 吃了顿早饭。Swisher 是一名科技记者,也是这个行业里有名的 “权力掮客”,人称” 硅谷最令人生畏也最讨人喜欢的记者”。席间谈话转向了电视剧《硅谷》。
“硅谷那帮人——至少是我认识的那些——常常聊起这部剧。”Costolo 告诉我,“奇怪的是,大多数人都很喜欢。我觉得有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在告诉自己,‘他们讽刺的是那些科技圈里的讨厌鬼,不是我。’” 人脉通达的 Swisher 跟该剧的执行制片人 Mike Judge 和 Alec Berg 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对 Costolo 说:“我把你介绍给他们。”
一个月后,Costolo 就得以跟 Judge 和 Berg 在洛杉矶共进午餐。他们告诉 Costolo,剧本创作已经陷入了困境。该剧讲述的是一个创业者如何努力起家的故事;而现在这个创业者被赶出了自己创立的公司,他们把不准剧情应该怎么发展。
尽管看上去充斥了大量闹剧式的情节和滥俗的搞笑桥段,《硅谷》实际上却做足了功课。Judge 和 Berg 认为走出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聘请一位顾问,从他那儿获取更多信息。但他们没想到的是,Costolo 表示很感兴趣。
“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知道这些公司怎么运作的人,并不需要一个真的在管理一家公司的人。”Berg 说。虽然有些大材小用,Costolo 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
《硅谷》大部分的拍摄地并不是在硅谷,而是在洛杉矶的一个索尼片场,但这两个地方属于同一时区。接下来连着三个半月,Costolo 每周一早上都会从旧金山打飞的去洛杉矶,下机了叫个 Uber 去 Culver City,在附近酒店把过夜用的行李放下,然后在编剧室里待上两天。
Berg、Judge 和其他十位编剧会把各种问题抛向他,有具体的也有宽泛的,不一而足。比如:董事会上最有权势的人会坐在哪里,什么会对向 Richard(剧中男主角)这样的创业者产生激励,而什么又会令他觉得备受挫败?
Costolo 说:
“我会跟他们讲我观察到的一个细节,或者我遇到过的某个人。然后他们眼睛就亮了,问我说,‘那是真的么?’”
渐渐地,Costolo 放开了,开始讲自己的笑话。“他们很周全地没有对我操之过急,” 他告诉我,“从 CEO 变成这房间里最没经验的人还挺好玩的。”《孵化 Twitter》是所有工作人员都读过的一本科技纪实书,是 Nick Bilton 讲述的关于 Twitter 公司的历史。
“有一次他们在争论在某个故事架构中接下去应该发生什么,”Costolo 告诉我,“Mike 问大家,‘那本 Twitter 书不是写他们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么?他们的决定是什么?’有人指出:‘Mike,那本书写的其中一人就坐在这个房间里。我们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不就行了。’”
《硅谷》目前已经播到了第三季,是现在荧幕上最搞笑的电视剧之一,也是各类作品中第一部野心勃勃想要展示北加州社会文化现状的讽刺剧。该剧的活力源自两种对立的态度:对财大气粗的科技巨头的鄙夷,和对试图颠覆的创业者的同情。
在试播集中,Richard Hendricks,一位腼腆但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发明了一种压缩算法能巧妙地减小大型文件所占的空间。后来借着这项发明,他成立了一家公司,并坚持称之为 Pied Piper。(Richard:“这可是个经典童话。” 员工:“这故事讲的是一个嗜血的魔笛手如何在山洞里杀了一群孩子。”)
随着公司逐渐发展,Richard 就像是一个科技宅男版大卫,饱受来自各种歌利亚巨人们的困扰:两面三刀的董事会成员、企图窃取他的知识产权的巨头。他能不妥协自己的价值观并且获得成功么?讽刺的是,想必 Richard 的最终目标就是自己成长为另一个歌利亚;如果这一点还没有被编剧论及,那就是暂时搁置避而不谈了。
Roger McNamee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风险资本家,同时也担任该剧的顾问。他告诉我:“你在剧里看到的操蛋事儿都是现实中的初创公司经历过的,有的甚至更扯。编剧有的时候不得不砍掉一些真实发生的事,好让剧情看上去更可信些。”
Judge 和 Berg 都很看重真实这一点。
在 Judge 1999 年的电影《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中,他就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或者亲眼所见到的一些细节来丰富主题——白领阶层的艰辛,比如老板过度重视 TPS 报告的排版格式,连锁餐厅强迫服务员在工作服上至少戴 15 枚徽章来表现餐馆的 “有趣”。
同样地,很多 Berg 编剧的作品,尤其是著名的《宋飞正传》,也从现实生活中获取故事素材。“在做《宋飞正传》的时候,这种情况出现了一次又一次。”Berg 说,“某个人会说出十个想法。头九个都是奇奇怪怪、傻乎乎的,而第十个总是很好笑、很有趣。你会问,‘这个想法是哪儿来的呀?’然后那人回答说,‘事实上那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
如果你在创作一部像《宋飞正传》这样没什么正题的剧,或是一部讲述办公室格子间文化的电影,要收集真实的细节素材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你想知道竞业限制条款该怎么设计,或者一个典型的直男癌码农会开什么车,或者 Richard 遭到驱逐是否会引发一下午的身心不适和个人危机,你就需要好好做做功课了。
一直以来,电视剧编剧都会向专家寻求咨询。比如,请医生展示如何拿除颤器,请军官确认制服的颜色没有问题。以前,这些顾问通常担任核实的角色,在剧本快要写好的时候被请来确认不至于有错得离谱的地方。
而现在,观众对电视更加较真了,有了 Twitter 和维基百科,一个个俨然都是评论家。Jay Carson 说:
“你再也不能拿不切实际又蹩脚的梗来糊弄观众了。”
Carson 曾在希拉里 · 克林顿 2008 年竞选总统时担任她的新闻发言人,也曾是洛杉矶的首席副市长。2011 年,他的朋友 Beau Willimon 聘请他出任电视剧《纸牌屋》的政治顾问。“我帮助咱们通过了华盛顿内部人士的测试,也通过了普通观众的测试。” 他说,“哪怕是在我在的那五年中,每一季观众都会比之前更精明。”
《硅谷》被认为是一部情景喜剧。“我们会开很多傻玩笑,但也花很多工夫让剧情显得真实。”Berg 告诉我,“我们希望硅谷那儿的人(作者注:比如说码农、亿万富翁,或者是两者兼备的那群人)看了这部剧后会说,‘我不喜欢他们拿我们开涮,但他们说的倒是没错。’”
现在 Richard 已经重任 CEO,而 Pied Piper 历经好几集的法律纠纷和继任危机之后重新得以一门心思、开开心心地去开发他们的平台。“公司创始人在重振团队士气上的能力是谁都没法比的,不管那些外援 CEO 的成就有多大。”Costolo 告诉我。
该剧一个经典的梗是第一季里一段为时一分钟的片段剪辑:创业者们纷纷宣称将通过 “Paxos 算法一致协议” 或者 “实现端点之间通信的正则数据模型” 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幕就摄于 TechCrunch Disrupt 大会,在这里创业者像在 “美国偶像” 中一样,向一屋子的投资人轮流展示他们的项目。
在写这一集之前,Judge 和 Berg 去旧金山的一次 TechCrunch Disrupt 待了一个周末。Judge 说,“你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资本主义伪装成嬉皮的样子,口口声声表示 ‘我们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直接说‘嘿,我们搞定这问题了,正发大财呢。’显得太俗了。”
这一幕播出之后,观众抱怨说剧中参会者缺乏多样性。Berg 回忆道,“我一个在圈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为什么没有女性?这太 TM 扯了!’我跟她说,‘没错!但很不幸,那一幕我们就是在真的 TechCrunch Disrupt 大会上拍的。’”
Berg 和 Judge 都拥有科技行业相关背景,所以他们比一般圈外人士更了解硅谷的文化。他们也倾向于启用有类似背景的编剧。
上世界八十年代,就在第一次 IT 泡沫破裂之前,Judge 是在圣克拉拉工作的一名电子工程师,负责设计显卡。Berg 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生物物理学家,而他的兄弟是一名程序员,同时也是一名创业者,“去了斯坦福大学读计算机研究生,就在离 Sergey 和 Larry 不远的地方”。
而这里所说的 Sergey 和 Larry 就是把自己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变成 Google 的布林和佩吉。
Dan Lyons 是《硅谷》第三季的一名编剧,曾经是一名科技记者,离开媒体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后来遭到裁员就这份经历写了一本回忆录《无疾而终》(Disrupted)。
另一名编剧 Carrie Kemper 于 2006 年毕业于斯坦福,并在谷歌的人力资源部门工作。那个时候,Kemper 发现她老板每天早晨的习惯包括用谷歌搜索自己的名字。这个梗就出现在了最近一集《硅谷》当中。(“我的每一天总是从在 Hooli 搜索引擎里输入我自己的名字开始。我喜欢这个小仪式,因为它以我为中心。”Hooli(一个类似谷歌的公司)的 CEO 说,“但最近,情况却恰恰相反。”)
这一季《硅谷》在索尼片场拍摄的时候我正好也在现场。不少人都怂恿我去跟 Jonathan Dotan 聊聊。现在本身作为创业者的他也是这部剧的首席技术顾问。“他就是那个看上去像 1947 年代在哈瓦那的骗子的家伙。” 编剧兼制片人 Dan O’Keefe 告诉我。确实如此,跟剧里剧外都穿着牛仔裤、球鞋的演员、编剧和其他剧组人员不同,Dotan 更喜欢剪裁合身的外套、口袋巾和五颜六色的正装袜子。
我在 Raviga 的办公室里等他。Raviga 是剧里虚构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它的装修风格——裸露的红砖,锃亮的不锈钢以及无处不在的地毯——跟我曾经到访过的 VC 办公室出奇得像,就好像多伦多的凯悦酒店跟在休斯顿机场的凯悦有着一致的审美风格。
为了让导演能够随心所欲地把摄像头对准任何地方而不穿帮,布景设计师打造了一整层的办公空间,在背景墙上挂上公司 logo,在接待室的茶几上面摊放着麻省理工的《科技创业》杂志(MIT Technology Review)——尽其所能地让这个地方看上去逼真。而其中很多房间确实被拿来当办公室使用,手头没事的剧组工作人员就坐在那些紧闭的玻璃门后面,敲着键盘或者打着电话——这就更令人辨不清虚实真假、戏里戏外了。
Dotan 把我带去了董事会议室。他试了两个假的插座然后找到了真的那个,把电脑插上电源,放在一张浅色木质会议桌上面,打开一份他准备的关于《硅谷》的研究流程的 PPT。“这份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技术参数方面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观众不会容忍一点差错。” 他说。
作为一部讲述计算机宅男的电视剧,《硅谷》的粉丝群特别注重细节,也特别容易就此在网上跟人产生争论。如果一张便利贴,一个 URL 或者一行代码在剧里能看清楚,这些人会截屏下来然后仔细研究。
去年,在其中一集播放后几个小时之后,一位网名叫 “他是我的负鼠” 的 Reddit 用户开了个帖子,问 “为什么编剧就这么毁掉了在它的核心观众中建立起来的良好口碑?” 他强烈表示,剧中 Piped Piper 服务器上面数据的意外删除这一情节显得很假。
“所以文件在 FTP 传输的同时也在被转码么?而这会影响硬盘内容的删除速度?…… 真他妈得了吧。”
作为顾问的 Rob Huller 本身也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登录了自己的 Reddit 账户,从技术层面进行回击来维护自己的作品。“这种事有时是会发生的。” 他写道,“我记得甚至连 Amazon 都发生过一次崩溃,缘于一位系统管理员的误操作使得某一时刻的 DNS 和 ACL 被改掉了。”
另一名用户回复他:“谢谢你在这里跟我们互动。感激不尽。” 这个帖子引起了将近三百条回复。“他是我的负鼠” 后来写道:
“抱歉,我之前有点二。”
Dotan 兼职了几个礼拜,然后开始全职。一开始,他手下带了四名工作人员:一个是文件压缩方面的专家,一个是帮忙写剧中电脑屏幕上出现的程序的 UI 工程师,一个科技行业的高管,以及一个起草合同的硅谷律师。
在第一季尾声,Dotan 所带的人手增加到十二名。“如果剧中有个人拿着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是真的完完整整写好的,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Dotan 说:
“我们不会去想‘怎样可以偷工减料而让出现在镜头中的东西也没什么差别’,而会想‘让我们把这一切尽量做得逼真,看看最终是否有好结果吧。’通常也确实如此。”
现在 Dotan 已是制片人之一,不仅在艰深的技术问题,在剧情和风格上也有着话语权。
第一季在竞争来临的高潮中结束:Pied Piper 的压缩算法遇上了对手。“编剧希望 Richard 突然来个灵感,这样他的技术就会好上一个数量级。”Dotan 说。“所以我们不得不想出一个突破来,重大但又不会显得很假。”
Dotan 打电话给 Tsachy Weissman,他的算法专家,也是斯坦福的一名工程教授。“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给我梳理了无损压缩沉甸甸的发展历史。”Dotan 说,“根据我的理解,基本上就是香农在 1948 年的时候利用码树从上至下地来进行文件压缩;而几年之后,霍夫曼则采取了从下往上的方式。”
Dotan 据此做了份 PPT 报告给 Judge 和 Berg。“他们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提到了从上至下和从下往上。那能不能从数据库的中间开始往上下同时进行?’所以我又去问 Tsachy,‘从中间开始怎么样?有这可能性么?’他没觉得荒唐,反而说,‘事实上,这想法很有趣,也许能行。”
在剧中,Richard 的” 从中间着手” 的灵感不是受斯坦福教授启发,而是被电视史上最复杂的丁丁玩笑启发。
作为工作的调剂,Pied Piper 的工程师开始讨论关于如何才能最快地帮一群人都撸上一把。(此事说来话长啊。)他们在白板上画各种示意图,不遗余力地阐述着。最后,有一个人建议最高效的方式也许是通过 “两边每边各站两个人,丁丁头碰头” 的方式 “一次撸四个人”。也就是说,“从中间开撸”。Richard 的眼睛亮了,欢快的背景音乐开始响起,他走向电脑开始编程。
2015 年,Weissman 召开了斯坦福压缩算法论坛,之后发布了一篇四十页的白皮书来阐述从中间进行压缩的意义。他的一位研究生 Vinith Misra,写了另一篇论文更清楚地进行了数学演算。
“显然,从中间开始的压缩方法不像它在电视里那么奏效。”Dotan 告诉我,“要真奏效了,那我们都是亿万富翁了。但我们跟 Tsachy 和 Vinith 达成了一致,万一他俩完善了这种方法,Mike 和 Alex 将会和他们一起分享诺贝尔奖。”
Dotan 现在管理着超过两百名顾问。其中一些人跟他一起在片场工作;多数人会在后期介入。大部分都是不领工资也不会出现在鸣谢之列。这些人包括学者、投资人、创业者,还有谷歌、亚马逊、Netflix 和其他一些科技公司的员工。Dotan 说:
“我可能会快速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跟他们聊上个把小时。”
剧里最好的笑话,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来自于这种持续的合作过程。“我会发些链接,就我听到的一些事给他们通风报信,罗列一些可用作梗的当下流行语。”Palo Alto 的投资人 Aileen Lee 告诉我。“而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就我所知,这儿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
《硅谷》里有很多科技圈内的小红人客串,但大多数观众不会注意到;即使发现,也是因为他们格格不入的僵硬表演。但即使是眼尖的观众也无法理解《硅谷》与真实硅谷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隐形关系网络。
除了 Dotan 手里的一溜儿顾问,Judge 和 Berg 和硅谷里的一些头号人物都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无论是公开地还是私底下,其中不乏一些为人幽默或者别有用心的亿万富翁。
这种讽刺的和被讽刺的谈笑风生的非正式关系在喜剧历史上可说是离经叛道。尤维纳利斯早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就发表了讽刺作品,但不见得跟他嘲讽的罗马皇帝们称兄道弟——他们其中一个还判他流放。我们也很难想象十八世纪伦敦的醉汉给讽刺肖像画家威廉 · 贺加斯当模特,或者乔治二世给乔纳森 · 斯威夫特的小说提供笑话。
Swisher 说她还在继续给 Judge 和 Berg“拉皮条”,把他们介绍给像 Dick Costolo 这样的圈内人士,因为事实证明这些人不仅对该剧有所帮助,而且 “也不会太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开他们个玩笑都不成”。
游戏公司 Zynga 的创始人 Mark Pincus 就是如此。“当他们说想在我们办公室见面的时候,我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是不是就只想处心积虑地把我们塑造成小丑?’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我们有这么一个你会路过的可编程控制灯光的走道,我有些退缩。这东西不太好解释。后来,我确实在剧里看到了跟这个走道类似的东西。不过,你看,这儿发生的很多事都很扯淡。所以也没啥不公平的。”
这种关系是共生的:顾问很快就在圈外也略有名气——Costolo 和 Pincus 即将在未来的剧集里客串——也有机会来自黑一把;而该剧的创作者可以收集素材,哪怕在他们没带笔记本的时候。“Mike 看上去安安静静、平易近人的,但他的脑子一直在转,记下所有的东西。”Swisher 告诉我,“作为一名记者,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一项技能。” 我问,为什么科技圈里的人会想跟 Judge 聊?Swisher 反问道:“那他们又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每个夏天,当前一季刚刚结束而下一季还没开始写的时候,《硅谷》的编剧和制片人会前往北加州来一次考察之旅。晚上回旧金山的酒店,白天则奔波于各种活动。比如早上去 GitHub 的办公室参观,那里的门厅是白宫的总统办公室一比一的翻版;中午跟 AOL 的前 CEO Barry Schuler 共进午餐;下午去 Menlo Park 的沙丘路参观世界上最具价值的风险投资公司;然后在 LB Steak 跟 Reid Hoffman(LinkedIn 的联合创始人)和 Mark Pincus 共进晚餐。
“有那么几顿饭,就我、Alec 和三四个亿万富翁一起。”Judge 告诉我,“我们就坐那儿观察。其中一个人可能是最有话语权的那个。有时其中一个人起身去厕所,然后其余的人就俯过身来开始说他坏话。” 第一季里有这么一集,两个曾经共事过现在互相掐架的科技巨头在类似 LB Steak 的一家餐厅里狭路相逢。这些人在决定百万美金的事情时毫不犹豫,但在寒暄上面却显得极其费力。除非你在现实中看到过,不然这种场景是很难在剧本中处理妥当的。
“他们问过我关于剧中那家虚构的公司的问题,比方说是否真的能融到钱。” 互联网先锋和著名的风险投资人 Marc Andreessen 说。“剧里所描述的这种技术,如果存在的话,肯定会产生很大影响。不过你能否把它发展成一个靠谱的生意?难说。但是,公平来讲,对于我们投的一半的公司,你都能这么说。”
在第一季和第二季中间,编剧在 Andreessen 办公室的大厅里等待拜访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氢弹爆炸的照片。(“这是让人们保持清醒的一个好方法。”Andreessen 的发言人这么告诉我。)然后编剧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在那里围着一张原木色的会议桌坐了一个小时,听 Andreessen 向他们 pitch 各种笑话。
“这些笑话倒也不糟。” 其中一位编剧向我透露,“那个会上,我密密麻麻地记了八页的笔记。我从来没听过有谁讲话像他这么快的。” 虽然 Andreessen 讲的笑话没有一个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剧里,但他解释的一个概念却演变成了第二季中的一幕。剧中的那位风险投资人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双方的对话是从 Richard 上厕所的时候她打断他开始的。
在一次去谷歌山景城总部的参观中,大约六名编剧和 Google X 的老大 Astro Teller 坐在一间会议室中。Teller 戴着一枚关节戒,把长长的头发扎成一束马尾。“我们的考察会议大多都很好玩,但这次却让人不太舒服。”Kemper 告诉我。GoogleX 堪称谷歌的 “登月计划”,致力于研究类似无人驾驶汽车这样很难实现但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
Hooli,剧中一家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公司,跟谷歌有一种奇怪的相似之处。(谷歌的创始人 Larry Page 在《福布斯》杂志上说:“我们希望做更多的事,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在第二季里面,Hooli 的 CEO 则说:“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有人比我们更能改善这个世界的地方。”)
在上一季中,Hooli 宣布了自己的 “登月计划”——Hooli XYZ 项目,它的实验尽是些荒谬的闹剧:用仿生手撸管的猴子,能把土豆发射到房间另一头的强力大炮。“他(Teller)说他没看过《硅谷》,但他又多次提到剧里出现过的细节。”Kemper 说,“他的潜台词是,‘我们这儿不干蠢事。我们做的事是真的会改变世界的,不管你要不要嘲笑我们。’”(我们无法找到他对此做出评价。)
Teller 一气之下起身结束了这场会议,但因为穿着旱冰鞋,他没能如愿实现戏剧性的离场。他一言不发地摇晃着走到门口。“接下来那会儿尴尬得很。他摸索着自己的 ID 卡,想把门打开。”Kemper 说,“感觉有过了一个小时。我们都拼命憋着笑。即使正发生着这一切,我知道我们都在想一样的事情:我们能把这一段放进剧里么?” 最后,这个笑话被认为 “太老套而不能用”。
在 1991 年《巴黎评论》的一个访谈中,Tom Wolfe 谈了谈他的讽刺小说《虚荣的篝火》。他想写一本书能够抓住最近的一波历史浪潮——用他的话说是 “处在金钱狂热年代中的纽约”——而且,他觉得唯一能够承载他这份野心的类型是基于观察的左拉式现实主义。他拜访了临时收容所,采访了检察官和坐过牢的人。“我不认为一位作家的凭空想象——不管他是谁——能够跟通过研究和报告所得到的结果相提并论。” 他说。
Dave Eggers 在 2013 年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里面用完全虚构的手段来描绘他所处的在科技狂热年代中的南湾。“我从来没有去参观过任何科技公司,也不怎么清楚一个公司是如何运营的。” 他告诉《时代周刊》杂志,“我也实在不想知道。”
Wolfe 的书里充斥着过多过于细节的事物,比如华尔街办公室里的一尊黄铜摆设,一杯伏特加鸡尾酒里面 “薄荷的样子”;而 Eggers 只能猜测一个科技公司的员工会给他的同事们举办怎样的聚会(给对葡萄牙感兴趣的人组织一次早午餐?),结果就是这本书是一则带有警示意味的反乌托邦故事,比起预言,更像是一个狂热的梦。
显然,Eggers 认为他可以凭自己的想象来批判互联网。但互联网并不同意。据 Felix Salmon 说,“Eggers 偏离真实太远,以致于他的书感觉都不像一部讽刺小说了。”Jessica Winter 写道:“Eggers 写了将近 500 页的小说来讽刺科技圈子,但他自己貌似却对这个真实的圈子不感兴趣。”
2014 年,Judge 参加了 Swisher 组织的 Code 大会。第二年,这个会议就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了《硅谷》中。Swisher 本色出演,采访了 Hooli 的 CEO Gavin Belson。Belson,该剧的头号 “反派” 人物,是一个综合性的角色——他身上有 Marc Benioff、Larry Ellison、Jeff Bezos 等其他人的特征。在 Swisher 采访的那一幕中,他反驳了针对科技巨贾们的精英主义的控诉。
“看看历史吧,” 他说,“你知道还有谁曾经诋毁一小部分叫做 “犹太人” 的金融家和进步思想家?” 这段剧中的讽刺情节,几乎是直接引用了现实。2014 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腰缠万贯的风险资本家 Tom Perkins(老牌硅谷风险投资基金 KPCB 的创始合伙人)写的信:“我在进步思想的中心旧金山写这封信。我请求大家注意纳粹德国对她‘百分之一’的人群——也就是犹太人——所发起的战争,跟现在针对美国的百分之一的人群也就是‘富人’阶级的斗争不无相似之处。” 要说 Belson 和 Perkins 真有什么区别的话,前者的突发之言相比之下至少显得更有品味。
有时候,把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编进虚拟作品里所需要的就只是把一篇新闻头条变成一个好笑的梗。反过来也可以:正如所有优秀的讽刺作家一样,《硅谷》的编剧偶尔会试着夸张现实来编成剧情,不料生活中后来真的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在试播集里,一个直男癌码农开发了一款叫做 “咪咪警报器” 的 app,帮用户找到最近的 “凸点的妹子”。“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这看上去像回事儿么,还是顶多是个傻玩笑?”Berg 说。在试播集制作万但还没播出前,两个名副其实的创业者发布了 “看咪咪”——“一款在用户盯着咪咪看的时候自拍的 app”。
在最近一集里面,Gavin Belson 要求律师凭空造出一套新的法律策略来让一个说他坏话的博主闭嘴。考虑到时间先后,这个设定不可能是对挑衅的风险资本家 Peter Thiel 对媒体 Gawker 的采取的法律手段的一种反应,但看上去真的很像。
在第一季里面,作为该剧对某个真实人物最直接的刻画,Thiel 被轻微地虚构成 Peter Gregory,一个聪明但有社交障碍的投资人。“我很肯定他觉得受到了冒犯,因为任何事情都会冒犯到他。”Swisher 说,“你很难想象有些人脸皮有多薄。”
不过,后来 Thiel 邀请了一部分剧组的主创人员去参加他在洛杉矶举办的一场派对,而且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他说他喜欢这部剧,对此我们很惊讶。” 其中一名制片告诉我,“他本人并没有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笨拙。” 也许 Thiel 真的喜欢这部剧;也许他只是想要证明自己开得起玩笑,哪怕实际上他不能;也许,他算了下要把 HBO 告倒闭很难,就还是亲近敌人吧。或者说,也许就好像硅谷里面其他的关系一样:一半私交,一半生意;一半坦诚相见,一半利益互换;一半胡萝卜,一半大棒。
Roger McNamee,一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很成功的科技投资人告诉我:“当我第一次遇到 Mike 的时候,我问他,‘你这么干到底是咋想的?’他的回答是,‘我觉得硅谷在价值观上面面临着严重冲突:一方面是乔布斯这一代人的嬉皮士价值观,另一方面是 Peter Thiel 这一代艾 · 兰德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我自己从来没能说得这么清楚——我还亲身经历过呢!”
McNamee 最近渐渐从他和 Bono(译者注:著名乐队 U2 的主唱)共同创立的风险基金(也是他最后一支基金)中退出;现在大多数时候,他带着他的两支即兴乐队——Moonalice 和 Doobie Decibel System——在全国巡演。
他继续说:“事实上,我们中的有些人,尽管听上去很幼稚,来这儿确实是想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我们没能成功。我们改善了一些东西,也搞砸了另一些。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接了手;而他们压根儿不管对错,他们就是来这儿赚钱的。”
在即将播出的一集中,McNamee 的名字出现在了一段关于竞争激烈的融资的独白中。这一幕拍摄的时候我恰好在现场。T. J. Miller,表演这段的演员,不得不停下好几次,因为说错了 “McNamee” 或者 “Vinod Khosla”。
“真有这些人么,还是你他妈在逗我?”Miller 这样问一位编剧。到了第六次尝试的时候,他都已经能创作出像模像样的类似名字了:“我跟 McMeenan Bartman Associates 谈过了。然后 Jim Goebbels 打来电话,我直接挂掉让他去语音信箱留言了。”
这幕拍完之后,Miller 走回到他的拖车房间,用一个蒸汽呼吸器来润嗓。“因为这个角色,现在我以一种很诡异的方式跟科技圈儿有了交集。”Miller 说,“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通过讽刺他们,你相当于在举着一面镜子。有些人看着镜子然后说,‘操,我们看上去真傻。’其他人则看着镜子说,‘哇,我看着真他妈帅。’”
Miller 饰演的是 Erlich Bachman,一个抽大麻、留着滑稽的络腮胡子的吹牛大王,把自己在硅谷的房子搞成了个科技企业孵化器。因为 Richard 是住在他家的时候创办了 Pied Piper,所以 Erlich 没做什么事就享有一小部分股份和一个董事会席位。“很多人告诉我,‘我就是我们公司的 Erlich。’”Miller 继续说道,“而我告诉他们,‘你知道这不是件好事儿,对吧?’”
《硅谷》于 2014 年在加州的红木城(Redwood City)进行首映。众多科技名流纷纷出席。在之后的庆功宴上,当服务生端上来一碟碟开胃小菜的时候,Elon Musk 向包括一位 Recode 记者在内的一群人发表了一通负面的评价:
“大多数初创公司就是一出肥皂剧,但也不至于是这样子的肥皂剧。”
《硅谷》的一名编剧事后告诉我,“这些人越是自以为是,他们就越有可能忽视一部关于他们生活的情景喜剧和一部纪录片之间的区别。” 但编剧似乎鱼与熊掌都想要:当他们说对了的时候,他们对该剧的逼真还原夸夸其谈;一旦没说对,他们就嘲笑任何把喜剧情节错当成事实的人。
“有些硅谷的大腕儿不知道该对这部电视剧报以怎样的回应。”Miller 告诉我,“他们吃不准是应该觉得受到了冒犯还是应该觉得受宠若惊。而且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演员有着他们从来不可能有的名气——毫无理由,但事实就是这样。这简直要了他们的命。”
Miller 在红木城(Redwood City)的庆功宴上遇到了 Musk。“我觉得他肯定很震惊我竟然没有拍他马屁——我当时也确实做不到,因为那时我没意识到他是谁。他说,‘关于你们的连续剧,我有些建议。’我说,‘不了,谢谢,我们不需要任何建议。’他就更震惊了。然后就在我们聊天这档儿,一位女粉丝走过来说,‘我能跟你照张相么?’然后 Musk 就开始凹造型——说实话,这挺悲催的——但她却把相机递给 Musk,然后开始跟我一起凹造型。这就好像,抱歉,哥们儿,我知道你是号人物——而且,在这个例子里,他也确实是号人物——但我是那个 3D《瑜伽熊》电影的演员啊,显然我才是她想要合影的人。”
如果按市值算的话,世界上最大的三家上市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微软。他们是慈善资本主义开明的代言人还是垄断巨头?“在现实中的硅谷,就像剧中演的一样,有人是真的志存高远,认为他们将要改变世界;同时也有人对自己的 app 夸夸其谈但显然他们自己也不相信。” 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负责人 Sam Altman 告诉我。
《硅谷》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这种复杂性,因为它的制作人员——正如所有有思想的人,包括硅谷中最有权有势的人——并不确定他们对于硅谷的感觉。“我摇摆不定。” 一名编剧兼制片人 Clay Tarver 如是说,“我跟这些人打交道得越多,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扯淡和贪婪,这儿确实有着一些激动人心和充满希望的东西。”
在即将播出的一集中,Pied Piper 的销售部门委托广告公司制作了一支自吹自擂却空无一物的广告。“任何人都能坐在桌子边上。” 旁白说道,“桌子是用来帮助人们聚集、分享的。这就是为什么桌子就好像 Piped Piper。”
在这一幕拍摄那会儿,Uber 发布了一支语调类似的广告:“原子。诞生于 138 亿年前,组成了从 BLT 三明治到所有的母亲,再到纽约市等等世上一切。直到最近几年前,原子和比特存在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然而,有件事发生了。在 Uber,我们问,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世界结合起来会怎样?”
在拍摄间隙,Richard Hendricks 的扮演者 Thomas Middleditch 和 Pied Piper 的软心肠 CFO 的扮演者 Zach Woods 一起在手机上观看了 Uber 的广告,笑得令人费解。Woods 挨着 Tarver 和 Dan O’Keefe 坐下来。当时 O’Keefe 正坐在帆布导演椅上,看着一组视频监控器。Woods 给他们看了 Uber 的广告,问:“你们是不是根据这个来编的?”
“事实上,这是我们写完那一集之后才出来的。”Tarver 说,“我们当时想的是另一个,一支 Facebook 的广告。”
“Facebook 那个用的是椅子。”O’Keefe 说。
“不会吧,”Woods 说,“当真?”
“现在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做这些。”Tarver 说,“它让我想起伟哥最开始的那些广告,他们想尽可能做得含糊其辞一些,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为这样的产品感到羞耻。”
“我认为这是这群人的做作和他们的高度市场渗透两者之间结合的结果。”O’Keefe 说,“由于每个人都在用,所以他们无需告诉你这个产品是干嘛的。现在做广告的目的就是让你用的时候感觉更好。”
Woods 和 Middleditch 被叫回去为下一条镜头的拍摄做准备。Tarver 说,“有人告诉我,在有些大公司里面,公关部门已经命令员工不许再说‘我们在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情地嘲笑了这句话。所以我猜,至少我们因为让人们不再宣称他们在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真的让这世界变成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
本文原载于 The New Yorker,由 ONES Piece 何聪聪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