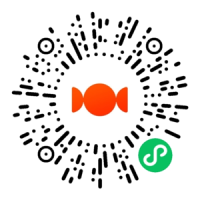对于美团及类型企业而言,这(骑手是否是雇员)是系统性、外部性问题,也是绕不过去的必然面对的问题。整体问题,有可能在美团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没有解决完毕。
曾经作为明星创业公司的 Uber,如今很难以新闻主角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了,尤其是其中国区业务被滴滴合并之后,大家对它就更无关注了。
最近关于 Uber 的新闻是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定,英国 Uber 的数万名司机会被归为「工作者(workers)」,将有权享受最低工资、假期工资,以及可能的养老金。当然,工作者(workers)和雇员之间还有定义的不同,后者享有更多权益。
而在 Uber 大本营的美国,加州法院投票通过 22 号提案,以允许 Uber、Lyft 等公司无需将司机归类为雇员。为通过该提案,Uber、Lyft 等共计投入约 2 亿美元,这也是加州历史上投入最高的提案游说活动。
众所周知,欧洲对互联网企业的管控非常严格,微软 Google 等企业都在这里吃过大亏,而美国加州则是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的沃土,对创新以及衍生效应的容忍度很高。所以就出现了英美两国对 Uber 截然不同的裁定。

在中国,其实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滴滴的司机该如何归类?
更迫切的问题是,美团和饿了么的外卖员,应该算美团或者阿里的雇员吗?
在美团的用工方式中,在美团上送外卖的骑手分为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众包为散工兼职模式,类似于大学生去超市打零工,这个争议较少。真正的争议点在于专送骑手,目前用工关系上是美图与第三方外包公司签以劳务为主流的合同,这样美团一来可以付出很少的用工成本,二来也能规避很多风险。
但事实上,因为对效率的追求,外卖骑手主动或被动交通违章酿成惨剧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当这些外卖骑手需要维权的时候,发现自己签署劳务合同的外包公司能够提供的保障寥寥无几,甚至此前饿了么还有克扣外卖员意外伤害保险金的恶性案例。
说到这里,解决方案似乎呼之欲出了:那肯定是要加强外卖骑手的安全保障和权益保障,不要用算法和效率压迫这些辛苦劳动的人,并且美团和阿里还要给骑手们签订直接的雇佣合同,为其缴纳社保医保等等。
有个类似的问题,大家也很清楚,就是关于孕产期雇员权益保障的。常理来看,大家肯定是希望用工单位给孕产期雇员更好地权益保障,比如产假要长,孕产期工资要高,陪产假也要长等等。但是如果这个权益太好了,用工单位成本很好,那么用工单位很可能在雇佣员工时对已婚未孕女性群体进行隐性就业歧视,以至于反过来伤害到这个群体的正当权益。所以,有时候,商业行为中,有些看似保护的行为,最终可能演化成伤害。
以上也不是为美团和饿了么进行辩解,实际情况是,企业的用工成本,最后肯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的良好体验,往往是又是建立在骑手极致效率上的。

如果有一家外卖公司,用心保护骑手权益,签订直接劳动合同,各种保障很全面,在安全和效率的天平上追求安全,最终结果是这家外卖公司的送餐费用多 3 块,并且送餐速度慢 10 分钟,消费者会更优先选择这家外卖公司吗?
答案显然是绝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更快更便宜的外卖服务,但也会要求外卖公司能够保障好骑手权益,还希望成本不要转嫁到自己身上。
这其中的复杂程度,已经不简单是企业、外卖员和消费者三者的博弈关系,更关系到类似于 Uber 司机改如何定义雇佣属性的问题,而英美之间的分歧,则说明大家还没有一个共识。
在财富中文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页面,简介为新融渡资本主管合伙人张国防的用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美团骑手用工话题,一个视角,其实是新型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匹配的过程量。
比如早期农耕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存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和雇佣关系;后来工业时代,「资本和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关系。相比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有劳动者法律和工会等工具保障自己的一定权益。
张国防认为,自 2007 年 iPhone 发布滞后,工业时代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数字时代变迁,但这一种新型生产力尚处于初级阶段,与之高度适配的生产系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外卖骑士是否属于美团饿了么雇员的问题就是一个具体表现。他说:
对于美团及类型企业而言,这(骑手是否是雇员)是系统性、外部性问题,也是绕不过去的必然面对的问题。整体问题,有可能在美团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没有解决完毕。
之前就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美团给旗下千万骑手缴纳社保,那么每天的支出将会增加百亿元,这对美团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更早之前,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则高调宣布,京东给旗下所有员工(包括快递员)缴纳了足额的五险一金,这样支出会比外包或者少缴多出 50 多亿。
往左还是往右,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王兴面前了,这不是发几句饭否能够解决的,但却是无限战争中的一个战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