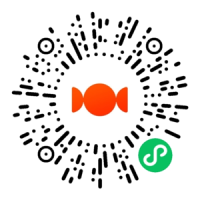音乐商人变形记 | 博望相
文 | 左蘅
图片 | SpaceCycle提供
采访 | 左蘅
编辑 | 小肥人

“接近天才的他小我几岁,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乐观、有勇气,但是在基本信仰的价值观上非常固执,像个小孩。但与他共事,我们从来没有起过争执,即使碰到意见南辕北辙的时候。熟识后,在我眼中成熟干练的马修,还是充满孩子气的。在办公室里他总会放着一两件男孩的玩具,遇到严肃的会议或棘手的问题,总是看到他把玩着他的玩具帮助思考,偶尔是一个球、偶尔是一架模型飞机……”——摘自姚谦《机场的遇见》

说实话,我对马修(Matthew Allison)知之甚少。坐在我面前的这位美国犹太人五十多岁,曾是台湾索尼唱片的创办人,因常年练习瑜伽,身材挺直、舒展。他戴着眼镜,穿着休闲 T 恤、牛仔裤,收拾得精致。
马修的父亲曾是大学老师,教英国文学,最常讲的是莎士比亚;后来辞职在纽约开餐厅,闯进了全美前十;60 多岁开始学中医,三年学成后在夏威夷开了十年中医诊所;75 岁时将诊所卖了一个不错的价钱。
马修的母亲热爱文学和绘画,懂得生活。比如他记得母亲将小小的自己放进浴缸,再把生日蛋糕也放进浴缸,供自己玩耍。
马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经济学和中文,毕业后工作了两年多,又在沃顿商学院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 MBA,毕业后收到了包括投行、迪士尼和索尼在内的 7 个 offer。他对理想工作的定义是,安定并有所成长。于是,他来到“薪资特别低”的索尼音乐——每月薪资相当于之前投行给他的住房补贴,并开始筹备索尼音乐台湾分公司。当时,他 27 岁。
“索尼音乐选择你的理由是什么?”我问。
“喜欢我。就是觉得我个性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唱片公司一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招数。”
马修在索尼呆了五年多,后入百代唱片,再后来在台湾开了十年瑜伽馆,去年又开了包括动感单车、Barre 和瑜伽三项课程在内的“音乐+运动”实验空间,今年他把大陆的第一家店开在了北京三里屯。
在这家名为 SpaceCycle 的空间内,马修和我谈他的从前。当然他的从前大部分跟音乐有关,现在的实验也和音乐有关。
今年九月,这家店的开业发布会上,嘉宾有音乐人姚谦、环球唱片大中华区总经理吴佳伦、索尼音乐中国大陆总经理胡译友、瑜伽大师 Paul Dallaghan 等等。明星则来了吉克隽逸和郑凯,前者显然跟投资人之一的姚谦有关,后者呢?SpaceCycle 的投资人中还有娱乐圈大佬。
音乐消费形态持续变化,从实体店到付费下载应用商店再到流媒体,现在,“歌单”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马修希望通过运动搭建新的音乐消费场景,在 SpaceCycle 的 APP 上,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歌单。他们有自己的音乐策展部,马修希望教练有音乐编辑能力,“可以根据情绪、时令、节日甚至当天新闻”来选择授课方式。
开业当天的动感单车体验课安排在一间雾气氤氲的屋子里,单车旁燃着香氛蜡烛,三位美国教练跟着音乐节奏肆意骑行。配合着声光效果,你会觉得他们是教练也是 DJ,这里跟热闹的 Party 大概只差了一个舞池的距离。
串烧的最后一段截自挪威电子音乐制作人 Alan Walker 的《Faded》,很长一段时间雄居我上班曲目 Top 10 榜单。那一刻,我想加入他们。
“我们就是把 KTV 和小型演唱会直接搬过来。”马修说。

天生商人
每次和马修一起出差,SpaceCycle 中国区总经理赵艳洁都是先过完安检的那一个,然后微笑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个美国男人从袋子里拿出瓶瓶罐罐,一个一个地摆在安检人员面前,“各种护肤品,营养品,擦的抹的。”
“你觉得他自恋吗?”
“绝对的。”赵说,“他就真的说,Sophia(赵的英文名)你不觉得为我工作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吗?很多人都觉得替我工作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当马修第一次跟姚谦聊 SoulCycle 并透露有意做这方面的事情时,姚就非常支持。既然音乐成了健身房主体,教练有自己的歌单,那就要与手握音乐版权的公司合作。“音乐这方面是我强项,”姚说,“台湾的 KKBOX 跟大陆的 QQ 都是我搭的线。”之后就是艺人资源,在台湾的 SpaceCycle,歌星庾澄庆和张惠妹都已经举办了几次粉丝见面会。今后,歌手还可以在这里举行单曲或专辑首发。
赵艳洁曾在华尔街工作,热爱健身。后来,她发现美国慢慢有一些小型的精品健身房出现,Boutique Fitness 开始流行。回北京投行工作后,马修有意让她参与自己的事业,赵一开始觉得他在开玩笑。后来一次去台湾,马修叫来各部门主管,每人为赵演示了一个半小时 PPT,赵当即决定加入。“当时他在台湾只开了两家 SpaceYoga,每年还要专门请会计公司来审计,完全是一个做大公司的感觉来做这件事情。”
在马修身上,赵同时看到了美国和台湾的那种“精益管理”,SpaceCycle 每天都要出一份细致的数据报告。
初入索尼,马修当时的上司是索尼音乐亚太区总裁。索尼音乐亚太区总部设在新加坡,上司让他在新加坡待一段时间,以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人。大概九个月时间,马修辗转于新加坡和台湾两地,在两家饭店间来来回回。期间,马修着手写商业计划,开始找人、选地点,筹备进军台湾市场。
后来,台湾公司“破纪录得赚钱”。“所以我得到非常大的权力在索尼,是可以做很多人家想不到的事情。”马修说。
他用“团结”来形容当时的公司文化,并坚持留出公司的旅游预算。那时公司很多人没有滑雪经验,甚至没有见过雪,于是马修组织大家到韩国滑雪。在最赚钱的 1996 年,他又带着大家跑到意大利。
在《机场的遇见》一文中,姚谦写马修从小受哮喘困扰,对他来说,长途飞行是种折磨。但为了争取一大笔去意大利旅行的预算,其“努力数月飞纽约与老板们奋战”。
马修曾对赵艳洁说,现在跟以前在索尼、百代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资源会主动放到你手上。
2014 年底,马修和赵开始在北京选址。“我们有地产中介,还有一些私人的关系。”赵说,在与商场的洽谈中,他们赶上了机会。自去年开始,一些奢侈品牌销售下滑得厉害,商场在选择入驻品牌的时候趋向多元化、体验型消费。“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些体验型的业态进来。”
“我虽然也问过国贸,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怎么可能承受得起那个租金,怎么可能?”但是采访时,他们在国贸三期的门店已经在准备中了。
姚谦带着赵见了 QQ 音乐副总裁,聊了一个多小时。“这个事情对于 QQ 音乐来讲,应该是太小了……还要资源、开发什么的,根本就是不可能。”马修甚至希望对方能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合作,“我们真的对 QQ 去提了(发布会的事情)!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肯定要被别人笑死,人家会想你是谁啊?!”赵笑着说,“但是他有他自己非常执着的地方。”
目睹马修与人谈判后,赵学到“最牛的一点,敢提需求、敢提条件。”虽然有些时候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姚谦觉得马修在北京应该招聘一个很好的秘书,“他永远都有很好的秘书、最顶级的秘书,必须执行能力很强。至于他的搭档,他不害怕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像我老是嗤之以鼻,他也能接受。他就‘哼’!我知道你觉得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我还是决定这样,他会这样告诉我。”
SpaceCycle 的声光效果由曾获格莱美奖的美国设计团队 3-Legged Dog 负责,这个组织聚集了一群艺术家,由几个主要人士负责接项目并掌控进度。凯文就是 3-Legged Dog 的一位负责人,也是美国犹太裔。因近些年国外经济不景气,以前常做大型艺术项目的他们也开始愿意在中国接一些小活。
“俩犹太人谈生意(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一个一个叹为观止。”赵说了一个细节,3-Legged Dog 团队第一次来北京看场地,半夜两点给赵打电话说一行三人已经把当天飞北京的机票选好了,请付款。赵问报销不行吗?对方说不可以。当时赵的美国信用卡已经无法使用,“半夜两点啊,第二天早上就没票了,真的一直能跟你杠着,就是不付钱。“
她给马修助理发邮件,正好马修还没休息。马修说”我也不能用我个人的信用卡付公司的费用,必须要第二天早上到银行付款。“于是两位犹太人互不相让,一直到凌晨四点半机票还没定。
赵和马修的助理都很无奈。幸好早晨时机票还没卖完。
但是后来二人见面时又非常友好。”公事就是公事,谈到钱的上面就寸步不让,就真的是犹太人厉害的地方。“但这显然不是赵的作风,她会自己先把钱垫了再说,她在公司的第一笔报销就高达 28 万元。”
马修在台湾创立索尼音乐分公司的最初三年,美国和日本的唱片公司还没有“经纪”的概念,但台湾的唱片公司有。姚谦说,那时候宣传歌曲主要通过电视台、电台和平媒,需要艺人配合,后来唱片公司开始考虑艺人造型,慢慢触碰到经纪的概念。
“那个时候美国公司艺人跟经纪是有冲突的,他们不赞成那个,他们怕里面有很多法律问题。”马修说,“一开始怕做艺人经纪不是我们的本业,觉得应该由经纪公司来做这个,我们纯粹就是唱片公司。”
但马修觉得在发掘艺人的同时不做经纪太可惜了,“太多事情本来就是我们的贡献,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好好地去建立这样一个部门?”
后来,他成功说服了公司。“我跟他们讲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做,为什么在台湾市场在法律方面没有他所担心的风险,我也给他举例别的公司开始做,是国内的公司不是国际公司,我们是第一个国际公司做这个的。”他举的例子中包括大陆的华谊兄弟。
离开索尼后,马修加入了百代唱片。在百代的最后两年,传统唱片销售急剧下滑,盗版越来越多,他将目标瞄准了“数位媒体”。“盗版市场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类似经验,因为数位媒体的权利是一开始唱片公司不肯放出来,它有很多害怕,因为这不是它的本业,我们开始用数位媒体的权利帮公司赚很多钱。”
“因为有这么多盗版,如果没有早投资这些(数位媒体),公司根本没有收入。公司数位媒体的权力让出去跟别人合资,或者跟别人做代理,开始把什么数位媒体俱乐部建立起来等等。”
每次马修说服别人的方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换位思考、知己知彼。“很多美国人怕的是法律上的问题,比方说像数位媒体,他怕这个东西会被盗版得更厉害,他怕他控制不住这个品牌,他怕对艺人是一个威胁,他怕他失去他跟艺人的关系。你要当一个好的经纪人,这也是一种教育。艺人不是怕这种事情发生,他怕他被欺骗,或者他怕你不跟他讲这个状况,或者是他怕你没有办法跟他说不。其实最厉害的经纪人是能够给艺人讲道理说‘不’,而不是一直答应艺人,答应艺人不是一个做好经纪人的方式。你要跟艺人像搭档似的,跟他一起实现他的梦想,你要配合着他去做到这个。如果你没有贡献,你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助理而已。”
姚谦形容马修:“一个实用主义者,典型的金牛座。”

识人
赵艳洁读过姚谦的那篇《机场的遇见》。“他说马修特别喜欢给人家制造第一次经历。我说好吧,那(来 SpaceCycle 工作)也是我的第一次。”
姚谦觉得这多少有点“强迫症”。他记得当年庾澄庆到美国录 MV,抵达的第二天大家还在倒时差,马修却买了很贵的黄牛票请二人一起观看 NBA 决赛。“硬带我们去看,我们两个睡得七荤八素的,然后什么都没看到。”姚说。但在马修的记忆中,只有姚在睡觉。他知道庾喜欢篮球,他希望可以送给他一份不一样的体验。
姚谦记得一次和马修去美国出差,入住一家旅馆时正好碰见影星茱莉亚·罗伯茨和他男朋友迎面走来。翌日早晨在健身房时又看到罗伯茨在跑步机上跑步。姚谦眼睁睁地看着马修将一个健身器械拉到距离罗伯茨不远的视线正前方,“开始各种练肌肉”。“我心想人家男朋友在边上呢,你在想什么呢!”姚在跑步机上直摇头。
姚谦的第一次 Around the World 旅行也是马修安排的。
认识马修的时候,姚已经在台湾点将唱片工作近十年。马修说跟姚谦接触一年后才有挖他的意思,但姚笑着说不可能,一开始双方就心知肚明。
对于当时的几大国际唱片公司来说,“华语市场一定要从台湾开始”,而进入台湾市场最快的方法就是并购,比如华纳曾于上世纪 90 年代并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飞碟唱片。除了飞碟,当时台湾引人注目的唱片公司还有滚石、宝丽金,马修则将目标锁定了点将唱片,但他面临一个强劲对手——百代(EMI)。
马修的计划搁浅在一位老太太手中。这位老太太是当时点将唱片老板的母亲,按照姚谦的说法,老太太以前不管事,只管钱。曾经他们接触过一家名称也带“哥伦比亚”几个字的外国公司,老太太觉得他们“不老实”,便坚持“不能哥伦比亚”。而马修所在的正是索尼旗下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姚说:“马修其实从头到尾几乎快到手,最后老太太说咱们别签哥伦比亚。”1996 年,点将唱片被百代收购。
点将唱片和百代私下达成协议的时候,马修找到姚谦,明确提出希望姚加入索尼音乐,那时候他们认识已经大半年。
姚谦觉得点将不会卖给别人,没有答应。年尾的时候,姚才知道木已成舟。马修第二次找他,姚说可以,但没有马上答应,他还不了解索尼音乐,况且每年都有其他公司来试探姚的意愿。
姚谦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在点将的交接工作,然后计划旅行,马修为他安排了一个 Around the World 行程——参观索尼音乐在多个国家的分公司,和当地总经理见面、聊天。
“那个是我最大的改变,回来的时候我就确定签了。”姚谦说。
Around the World 可以说是索尼音乐的一项传统,马修将其比作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他当初是这样,姚谦也是这样。“跟着当地部门高级主管,了解他们的管理心态,他们如何经营,怎么做,以及困难是什么。了解不同的经营模式,了解这个人、当地文化非常有关系。了解每个艺人的想法,了解公司怎么制约他,了解维持一个创意的制度是什么,怎么保留人的创意、人的贡献、人对公司的投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平衡。”马修说。
马修在四十周岁生日时和好友、瑜伽大师 Paul Dallaghan 一起到波兰参观了二战集中营。五小时参观最后,他在人群中瞥见一对年轻的台湾人,他们正在美国读研究所,台湾女孩对那段历史了解得相当全面。听了女孩的讲述后,马修改用中文说话,并希望女孩推荐几本相关书籍。
后来马修专门买了中文版送给姚谦。“世界有太多事情真的是轮回的。我对犹太人这一代的历史是透过一个台湾人了解,然后我又把它们推荐给另一个台湾人。”
第二次见马修,他刚面试完一位美国教练,面试内容是让教练为他们上一堂内部 Demo 课。上完课后马修花 5 分钟冲了个澡。15 分钟后,他要赶往机场,回台湾一趟。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理解他。看他的日程表就从 10 点一直排到晚上 8 点,星期六星期天也是。”赵说。姚谦也说自认识马修开始,他一直把行程排得很满。一次二人去日本出差,由于行程太满,最后赶飞机的时候只能“疯狂”地包一辆车。“我记得他跟那个保守的日本人说,你能开多快就开多快,我赶飞机。我都吓死了,然后给了四万多日元。”
因常年居住台湾,马修说中文时都带着明显的“台湾腔”。他读书的时候正好是华语流行音乐最丰富的年代,“从苏芮到罗大佑,到李宗盛都有听,后来很多艺人都是我们培养的,有很多年的关系,一直从庾澄庆,到李玟,到萧亚轩,到王力宏,到陶子……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最困难的事情大概是我必须要慢慢地进到国语的(环境和市场),培养国语艺人,因为我不能一开始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了解不够。”
马修口中的“慢”,一般大约是“一年”。他记得邀请李玟并不轻松。“那个时候 CoCo(李玟),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她妈妈、她姐姐(沟通)。她那个时候在一个香港的唱片公司,他们签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合约,所以我也必须要帮她们克服。我找了很多人,也找律师……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帮他们处理。”
后来马修开始负责大陆和香港市场。那时候索尼跟大陆很多音像出版公司合作,其中最大一家公司的老板后来跟着马修加入了百代。
马修记得索尼在大陆签的第一个歌手是刘欢。
他说相比港台,大陆更能接受艺人的多样性。
“怎么说?”我问。
“看刘欢就知道了。”
在马修的职业生涯里,很多时候是跟着人走的。后来,姚谦离开索尼,他说:“我是因为马修而离开索尼的,他到了百代,他不敢跟我联系,一年之后就出现了,我就辞了。”
姚谦唯一的条件是不喜欢“百代”这两个字,“觉得很老”。1992 年,维京唱片公司被创始人理查德·布朗森卖给了百代唱片集团。马修答应了姚的要求,说你可以用维京这两个字。于是,1998 年,姚谦在台湾成立“台湾维京音乐”。
“先做朋友,建立信任,再做生意。”马修说。
离开索尼前一年,他结识了维京唱片创始人之一 Ken Berry,当时维京唱片是百代唱片子公司,对方有意邀请其加入百代。“我大概考虑了一年我要不要做这个选择,因为离开索尼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责任,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我考虑了一年。”
维京的风格是马修没有经历过的。“索尼的高管,老板一定是开公司的飞机,好几个人一起来,一定要约很多的、可能跟很大的企业的会。那我(维京的)老板来的时候就穿了一个牛仔裤,带一个袋子,他可能睡在我家,我们一起去爬山,去享受葡萄酒,一起聊公司的事情。”
刚入百代的时候,马修 32 岁,管着几千名员工,30 几个公司,分布在 18 个国家。马修的目标是一年赚 2000 万美金,但实际情况是,第一年赔了 2000 万美金。
接下来的一年,马修每个礼拜会出现在三四个国家,了解每家分公司的经营状况。两年后,公司结束了赔钱的状况。
姚谦记得很清楚,一次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他见马修接完电话后脸色一下变了,才知道马修母亲去世了。
马修生母离世的同时,整个唱片业正急剧下滑,马修的上司 Ken Berry 被股东换掉,马修也跟着离开。“如果那个人不在那个系统,那个系统会变很多。如果那个人在的时候,可以继续发展。”马修说。
“维京和百代整合在一起后,业绩一直不好。所以股东就要求总裁换掉,他是核心的之一。回头看,是产业在变化。”姚说。
“退休”后,马修在 37 岁的时候搬到了夏威夷,在那里过了两年多自在日子,“投资房子,遛狗,种菜,做瑜珈,游泳,照看我的家人……然后就更了解我自己未来的野心要往哪个方向,我自己要做什么。”
马修 11 岁在父亲餐厅打工时经常见到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后来还见到了穆罕默德等。得益于“小孩子”的身份,这些人都乐意跟马修互动,跟他说话,马修说这让他“不会害怕陌生的东西”。

“把卡拉 OK 颠倒过来”
即便离开音乐圈,马修这些年和圈子仍有深深浅浅的联系。“大概每几年,我有机会回到音乐圈,都是跟着别人做一些他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有名的音乐家找他一起开公司,或者邀其当经纪人,或者开发新产品,“每两年都有这样的机会”。
马修一度不太喜欢健身房,因为“没有灵魂”。后来有一段时间父亲生病,马修考虑回美国。那段时间,他的一位朋友、投资健康类基金的老板告诉他,美国的健身房变了很多,你应该去认识一些新的精品的运动方式。
“他愿意分享很多东西给我,从科学,从投资人的概念,从很多数据什么的。另外,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去健身,我会找一些地方体验很多新的模式。”后来,马修终于确定,精品的运动方式正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件事。
当然,这个确认过程同样用了一年。
“上这些课,留给我最深刻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老师有没有魅力,老师有没有办法感动我;第二个感动我的,就是上完这些课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还在想老师怎么用音乐,我会一直听音乐的副歌。”
为什么上完课后对副歌念念不忘?他的答案是“老师的教学跟音乐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感动的力量正来自于这个结合。”
他脑中的灯泡亮了!
他对健身房的“进化”也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之前,健身房是靠硬体,靠机器,是一个‘壳’的概念。慢慢地,我们靠自己的体重训练,你做任何运动它都包含这个概念,所以可以缩小一个健身房的面积,可以从三千平方米缩到三百平方米。然后它可能像一个停车的工厂,它可能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我们所以为的健身房。那我就开始考虑去做这个(精品健身)。”
当卡拉 OK 开始占领华人娱乐生活的时候,马修刚好在唱片公司工作。他看到了卡拉 OK 是如何改变中国人的社交和娱乐模式的,他也将此看作一个新的音乐推广渠道。
现在,他希望“运动+音乐”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迫使自己运动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音乐是一个听力的视觉,那个感动的力量来自于我们一边推自己,一边感觉很脆弱。所以我们运动的时候特别敏感,特别容易被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人有力量的事情,我喜欢。”
赵艳洁告诉我,SpaceCycle 的一位教练在骑动感单车的时候泪流满面。马修觉得音乐可以成为新的动力,“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在室内运动场所维持运动的习惯。因为这个对我们的灵魂是没有支持的,那个支持来自于我们身体的健康(诉求),所以我们逼自己做。你看一半的健身房,大概 70%—80% 的人没办法坚持超过一年。”
基于以上原因,马修说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健身空间,而是卡拉 OK。
但也可以合作。SpaceCycle 位于国贸三期的新址就和一家量贩式卡拉 OK 毗邻。“不一定是击破他们,我觉得是搭便车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用同样的 DJ,DJ 从我们这里就坐手扶电梯上来,然后继续在卡拉 OK 做,然后带一批人上去,我们互相支持。”
马修说,未来,教练也可以出单曲。
“要把教练打造成网红吗?”我问。
“我觉得有可能,以中国的社会是有可能。”
马修 18 岁的时候遭遇过车祸,“所以造成我有一点长短脚,衰退的那只脚是短的。”他说。他记得自己练的第一个瑜伽动作是“拜日式”,一般人跪下时臀部可以贴着脚后跟,但马修的臀部离脚后跟还“很远”。“我就在那里觉得我一直在忍、忍,我没有办法忍太久,因为太痛。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应该去尝试的东西。我想体验到一些突破,我可以感受这是什么。”
曾经,他一天可以喝 6 到 8 杯咖啡。“越喝越觉得它的影响越来越短,对你也没有什么效果了,你喝得还很多。”后来,他在意大利断食一个礼拜。离开罗马时,他仪式般地喝了最好的咖啡,然后,便十年再没有沾过咖啡。
现在,马修又开始喝咖啡了,只不过已经可以严格控制在每天 1 到 2 杯。
“我刚刚送了朋友一本书,一个作家叫 Viktor E. Frankl (维克多·弗兰克),他写的书是排在美国前十名的畅销书。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叫 Man’s Search for Meaning。”在那本书中,作者叙述了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并指出“根据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途径来发现生命的意义:(1)通过创造一种工作或做一件实事;(2)通过体验某件事或遇到某个人;(3)通过我们对于不可避免的态度。”
“他的概念是,人类需要一个超过他自己的一个更大的意义生存。我觉得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马修说。